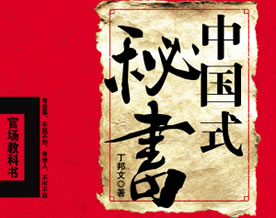从欢乐英雄到历史受难者——评《亮剑》
来源:左岸会馆 作者:刘复生
摘要:在当代小说中,《亮剑》也许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例:一部业余作者的处女作,1999年出版以来,风行网络,继而成为一再重印的畅销书,伴随着同名电视剧(根据其部分内容改编)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的播出,它…
在《亮剑》中,李云龙,以及孔捷、丁伟、“和尚”等,他们无时不对战斗,尤其是短兵相接的搏杀充满渴望与迷恋。正因如此,对他们而言,和平年代完全是平庸乏味、不可接受的。对于这些革命者、英雄来说,战斗似乎是一种个人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更高、更完美的社会秩序,也并非基于某种政治信仰或理想。这些出身社会底层的革命者缺乏对自身战斗的最终目标及其宏大意义的认知,小说凸显身体与性格这些相对来说缺乏精神、思想深度的个人特征,他们的政治理想、内在精神境界始终是缺席的。小说没有出现这类心理描写,也没有设置专门的情节或人物语言来显现这种内在精神——他们甚至连一点这样的朴素想法都没有。与他们干瘪的内在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他们过于充盈的身体:强健而富于男性魅力。
革命英雄的身体不再由肉体向精神升华,他的身体是自足的,并不需要由另外的、来自肉体深处的理想性的光芒来照亮。但是,他的身体仍然是升华的,即肉体向着其自身高度完美的形态升华,它与其内在的精神性因素无关。在《亮剑》以前的小说《我是太阳》中,已经出现过主人公负重伤之后神奇痊愈的重要情节:关山林被炮弹炸飞,身体几乎被“炸烂了”,但是,仿佛任何重创都不能损伤关山林的身体,七天七夜之后,他又神奇地“活了过来”。《亮剑》也重复了这个套路,甚至连李云龙与关山林受伤和康复的方式都一样(被近距离枪弹击中,七天后苏醒),历尽枪林弹雨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生还,很快又活蹦乱跳了。
这种处理使英雄的躯体显示出某种非肉体性。的确,在小说中,很少对于英雄身体感觉的书写。受伤,虽然是濒临死亡的重伤,对李云龙来说,只是一次短暂的记忆中断,醒来后,他依然拥有完美、强健的身躯(小说此后也没有写到这些重伤留下的后遗症,直至壮士暮年,依然精力充沛,身强力壮),能量未受任何损伤。于是,在这里,英雄的身体实现了一次隐秘的升华,它使身体超越了生理学,脱离了肉体的实在性,被抽象化为一种完美的躯体。那个身体中的身体是不可摧毁的。
这一方向上的升华已完全不同于旧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对英雄躯体的“升华”方式。虽然仍带有一些对革命英雄意志的赞美,但小说表达的重心显然已经偏移。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对肉体的“升华”是为了追求精神、灵魂的绝对深度,那么《亮剑》对肉体的“升华”却只是为了强调(男性)肉体自身的魅力。
这就使英雄起死回生、神奇复原的二重或多重生命具有了某种游戏色彩。从中可以发现《亮剑》式的“升华”形式已经渗入了所谓后现代时代大众文化的幻想逻辑:其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形式是电脑游戏,其中的英雄即具有多重生命,遭受重创或“死亡”之后还可以重新完好如初地恢复自身的能量。其实,这种幻想逻辑正是大量科幻片和动作片的前提与预设。③《亮剑》巧妙挪用了电子时代的大众文艺幻想逻辑及其表现技巧。
非常清楚,《亮剑》虽然在形式上是革命历史小说,实际上却远离革命,成为一部热衷于暴力搏杀的动作片。
另外,《亮剑》的故事与人物关系也是高度好莱坞化的。
在性别关系上,《亮剑》相当陈腐地重复了一个美人爱英雄的套路,在项羽式的英雄李云龙和江南美女田雨之间,爱情只意味着美女迅速地被英雄的强力的男性气质所征服,并死心塌地地从一而终(在李云龙死后自尽),决不拖泥带水。这种过于清晰和直截了当的男性中心主义使它区别于《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在天堂等你》、《父亲进城》,甚至《我是太阳》的写作套路:它们也都设计了粗鲁的军官与带有“小资”知识分子气质的美女的爱情,但它们显然将兴趣放在了美女对“大老粗”革命者由拒斥到接受的漫长的戏剧性过程上,在性格、知识修养以至生活方式上二者都产生了持续的冲突。《亮剑》决不屑于过多留恋狭小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家庭),更不能容忍美女对英雄的拒绝(哪怕仅仅是在一开始),这磨损了英雄的无穷男性魅力,女性只不过是印证男性强力的价值客体罢了。尽管在《亮剑》中,也有一点似乎不可不有的优雅的生活格调与农民式的生活趣味之间的冲突,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点可有可无、一闪即逝的情节点缀罢了。可以说,在性别关系上,《亮剑》毫无创造性可言,完全是好莱坞式动作片的模式。
《亮剑》还加入了兄弟情谊的书写(李云龙与政委赵刚,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前一组关系使代表党的政委和作为革命军队指挥者的师长之间的关系化为江湖兄弟的关系,成为《英雄本色》式的义气。小说及电视剧都弱化了赵刚的意义:军队就是打仗的。《亮剑》对带有书生气的赵刚进行了揶揄。最后,有意思的是,赵刚被草莽英雄李云龙所征服、改造,包括性格与生活方式(粗话骂人,喝酒)。这又改写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反转了政委与军事指挥员的关系,不禁让人怀念起《铁道游击队》或苏联的《恰巴耶夫》(《夏伯阳》)所显示的经典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云龙与敌手国民党将领楚云飞之间惺惺相惜的兄弟情谊(当然,在当下,国共两党的关系已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这是既往的一切新旧革命历史作品所不曾有过的。这一处理是充满大众文化味道的,依据的正是好莱坞式的大众文化的逻辑:对手之间的兄弟情谊是当代动作片的经典模式,吴宇森的《喋血双雄》无疑是这种模式的经典代表。通过这些方式,革命斗争及其内在价值就转换为江湖历险及兄弟义气。